(一)戀愛推理小說
《人造衛星情人》是村上春樹難得一見的長篇戀愛推理小說,故事描寫一位 22 歲女子小菫有生以來的第一次戀愛,村上春樹如此描述:「就像筆直掃過廣大平原的龍捲風一般熱烈的戀愛。那將所到之處一切有形的東西毫不保留地擊倒,一一捲入空中,蠻不講理地撕裂,體無完膚地粉碎。而且刻不容緩毫不放鬆地掠過大洋,毫不慈悲地摧毀高棉的吳哥窟,熱風將印度叢林中整群可憐的老虎燒焦,並化為波斯沙漠中的狂沙暴,將某個地方少數民族的城邦要塞都市整個掩埋在沙裡。一個壯觀的紀念碑式戀愛。至於戀愛對象則是比小菫大 17 歲的已婚者,再補充說明的話,是一位女性。這是一切事情開始的地方,也(幾乎)是一切事情結束的地方。」這樣的疑問語碼(Hermeneutic Code)深深吸引著讀者。
所謂「疑問語碼」,這是傳統小說最常見的語碼,一般說來,傳統小說的最大興趣是「說故事」,誠如英國小說家佛斯特所言,說故事離不開「想知道後事如何」,讀者不斷地提問:「然後呢?」此乃人之常情;就故事本身來說,它只有一個優點:使讀者想要知道下一步將發生什麼。提出懸疑和問題,可以挑逗起讀者往下看的興趣,而小說發展下去則是要解決懸疑。換言之,小說的閱讀是從疑問的產生到疑問的全部解決,此疑問語碼正是構成小說懸疑的主要因素。
村上春樹《人造衛星情人》透過人物互動的抽絲剝繭,特別是小菫的突然消失無蹤以及心愛的妙妙一夜白髮,終於明白小菫的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的戀愛,並且為書中人物寧願永遠活在夢世界的那種孤絕而萌生同情。
(二)我愛小堇
《人造衛星情人》主要人物有三,包括敘述者「我」、「我」暗戀的小堇、小堇所愛的妙妙。「我」、小堇及妙妙三人的視點幾乎是對等的,有時候獨立,有時又是緊密結合在一起進行,村上春樹嘗試以「移動小說的視點」來推展情節。
24歲的「我」是小堇口中的怪人。「我」來自普通家庭,在東京都出生,於千葉縣長大,父親在一家大食品公司的研究所上班,母親喜歡創作短歌也喜歡打掃,但討厭做飯;比「我」大5歲的姊姊則打掃和做飯都討厭,所以「我」懂事之後,學會自己下廚。姊姊功課好,東京大學畢業第2年就取得律師資格,姊弟關係十分疏離,家人也完全不關心「我」,因為「我」對功課沒興趣,成績馬馬虎虎。「我」幾乎沒有跟家人親密地談過話,不了解同住一個屋簷下的雙親和姊姊是什麼樣的人,以及他們對人生又追求些什麼。事實上,「我」也一直困惑著,所謂我是什麼?我在追求什麼?要往哪裡去呢?上了大學,「我」主修歷史,畢了業,剛好有機會當上小學教師。「我」本來並沒有想當老師,但實際試著當了教師之後,發現居然對這份工作比自己所預期的懷有更深的敬意和熱愛。
「我」從小就像是一直一個人活著過來似的,經常想像遠方某處,有一棟房子,住著「我」真正的家人;房子雖小,卻是讓人心安的家,在那裡每個人的心意可以很自然地彼此相通,任何事情都可以很坦白地說出來。事實上,「我」的心始終無法敞開,不管對任何人都保持一段距離,未對誰有所期待;既然沒得到什麼,因此就不會有擔心失去什麼的問題。「我」對世界毫無保留的熱情,僅限於在書本和音樂中才看得出來。「我」算是孤獨的人,唯有和小堇見面談話時,最能活生生地感覺到所謂「我」自己這個人的存在。「我」在大學比小堇高兩年,於大學正門口附近的巴士站因閱讀的西洋小說而結識,原來兩人都像呼吸般自然地愛看書,「我」除了自己以外,從來沒有遇到過這麼深入廣泛而熱烈讀小說的人,對她來說也一樣。而且以小堇來說,願意把自己寫的稿子給別人看的對象,在這廣大的世界僅僅「我」一個人而已。「我」和小堇一見面,總是花很長時間談話,話題談不完,談小說、談世界、談風景、談語言,不管談多久都不會厭倦,可以說比一般戀人聊得更熱心、更親密。「我」一方面傾聽小堇說話,一方面因擅長說明事情,不時為小堇解決疑惑,幫助她安定心情,成了小堇最信賴的人,唯一的、完全的朋友。「我」也因小堇而不感寂寞、孤獨,小堇對「我」來說,是多麼重要而不可替代的存在。「我」和小堇可以很自然地心意重疊相通,兩人就像一般年輕情侶脫掉衣服赤裸相對一樣,可以把彼此的心敞開來讓對方看,那是在別的場合,對別的對象,所無法體驗到的事;兩人為了不破壞這種心情,彼此都極珍惜細心地相處著。
「我」經常在想,跟小堇如果能成為戀人,該有多好。縱然小堇喜歡「我」,但那種喜歡卻有別於一般戀愛男女之情,也沒有所謂性的關心。小堇真正喜歡的是妙妙,她明白告訴我:「我對她所感覺到的感情,跟對你所感覺到是不同種類。」儘管小堇愛的是女人,不過,「我」依舊比誰都愛小堇,對她仍然有著強烈的性慾望,無法停止那種愛撫的妄想與相交的想像;這種想像中的感觸,甚至於比「我」和別的女人實際做愛還更加真實。無法跟小堇分享肉體的喜悅,對「我」來說非常痛苦。兩人之間,其命運註定不會有結果。儘管如此,「我」並不放棄,仍夢想著有「突然大轉變」的一天。
為了減輕痛苦,「我」開始和其他女性發生肉體關係,這些女性對象年紀都比「我」大,有先生、未婚夫或男朋友。跟她們身體接觸的時候,「我」經常想到小堇,也曾想像自己抱著的其實是小堇。最新的性愛對象,是「我」帶的班上學生的母親,跟她每個月有兩次,悄悄約會睡覺。學生的母親比「我」大7歲,已跟丈夫將近1年沒有性生活。但「我」無法愛她,因為和小堇在一起時,那種毫無條件的自然親密感,跟她之間卻無論如何都無法產生。每次跟她見面之後,只會更加確定,自己是多麼需要小堇。
當小堇和妙妙一起去歐洲旅行,接著在希臘突然失蹤,即使開學在即,「我」仍排除萬難,應妙妙要求前去希臘協尋,告訴妙妙,完全是基於個人的自由意志來到這裏的。可是,終究找不到小堇,報警也一無所獲。經由妙妙的說明以及透過小堇的磁碟片文件,「我」約略知道,小堇的失蹤與其向妙妙告白而遭拒絕有關。「我」覺得,自己大概再也回不去原來的自己了,心中有什麼已經燃燒殆盡、消滅了。回國後,學生的母親向「我」求助,幫忙去警局處理學生偷竊事件;為了感覺相當敏銳的學生和周邊其他人設想,「我」主動向學生的母親提出分手,以免自己變成問題的一部分。而「我」也想,和住在東京的妙妙一樣,各自繼續活著,不管多麼深刻致命地失落過,不管多麼重要的東西從自己手中被奪走過,或者只剩外表一層皮還留著,其實都已經徹底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了。
「我」依然作夢,活在夢中的世界,夢見小堇回來,感覺作夢彷彿是唯一做對的事似的。果然,小堇已經回日本來了,深夜打電話給「我」,要「我」去接她,卻又唐突地掛斷電話,但「我」想「我們正看著同一個世界的同一個月亮。我們正確實地以一條線聯繫在現實上。我只要安靜地把那線繼續拉近就行了」,因為「我」已經準備好了,可以隨時到任何地方去。只是,即使又和小堇在一起,她同樣不太可能改變自己是同性戀的這種宿命,「我」註定還是得繼續忍受著痛苦與悲哀。
(三)小堇愛妙妙
《人造衛星情人》的關鍵人物小堇,22歲。父為橫濱市開業牙醫,長得特別英俊,很受女性患者歡迎。小堇還不到3歲,母親病逝,當時母親才31歲。小堇這個名字是母親所取,因為母親最喜歡莫札特的歌曲〈堇〉,即紫羅蘭。可是上了中學,在學校圖書館找到歌詞的日本語翻譯,小堇深受打擊,原來歌詞內容是說,開在原野的一朵清新美麗的堇花,被某一個粗心大意的牧羊女無意間悲慘地踐踏了。自己成了被踐踏的花,這名字是母親留給她的唯一有形的東西,卻讓她好失望。小堇6歲時父親再婚,兩年後弟弟出生。小堇從神奈川縣公立高中畢業後,進入東京一家私立大學文藝系,只是大學校風保守,令她失望,周圍的學生大半都是無可救藥的無聊而平凡,因此小堇上3年級以前就乾脆休學,準備寫小說,以免浪費人生。這時,支持、鼓勵她的是繼母。繼母花時間說服父親,同意小堇於28歲以前仍由父親來負擔生活費,使她能夠繼續閱讀和集中精神寫小說。
關於小說,小堇對19世紀長篇大論的小說深感興趣,想把繞著靈魂和命運打轉的一切事象,巨細靡遺地填塞進去。結果自始至終,小堇沒能完成一篇小說作品。她覺得,自己天生缺少當一個小說家的必要質素,但「我」鼓勵她,說她的文章是有生命的,有好像它自己會呼吸會動似的、自然的流動和力量,流露獨特的新鮮感,可以感覺到,想把自己心中某種珍貴東西寫出來的坦率與用心,這並不是誰都會寫的,風格也不是模仿誰的。雖然還寫不出完整的東西,妙妙同樣肯定小堇的才華,說:「將來一定可以寫出傑出的東西。不是客套,我真的這樣想。我可以感覺到妳身上有這種自然的力量存在。不過現在的妳,還沒有準備好。還沒有準備好打開那扇門的足夠力量。」
小堇的父親英俊,她卻矮小、不美又不化妝,平時穿著邋遢。雖然如此,在「我」眼中,小堇還是有某種吸引人心的特別東西,很難用言語說明。妙妙則認為小堇非常漂亮,絕不會輸給父親。個性方面,小堇既頑固執迷又習慣嘲諷,不懂人情世故;喜歡像山林監視人那樣的工作,每天站在山頂上俯瞰四方,然後痛快地看自己喜歡的書或是寫小說。事實上,她沒有正式的工作經驗,只曾經短期打工。在家中,不會煮飯做菜、不會打掃、不會整理東西、老是掉東西;雖然喜歡音樂,唱歌卻荒腔走板;方向感簡直是毀滅性的,左右經常搞錯;一生氣就有破壞東西的傾向。她也沒道理地怕生,幾乎沒什麼朋友。唯有與同樣喜歡閱讀的「我」成為知心朋友,但這不是男女之愛。小堇在高中時代有過性行為之類的經驗,那不是由於性慾或情愛,而可能是由於文學上的好奇心所引起的。總之,她對男生就是沒性趣。
跟妙妙就不同了,她們在小堇表姊的婚宴同桌而一見鍾情,相談甚歡,小堇感覺周圍的空氣忽然咻一下變薄似的,心裡知道,「也許將被帶到一個自己從來沒看過的特別世界去。那或許是個危險地方。藏在那裡的一些東西或許會帶給我深深的、致命的傷害。我或許會失去現在所擁有的一切東西也說不定。但我已經回不去了」。一想到要跟妙妙見面,小堇心裡騷動不已,什麼事情都做不下去。只要能夠跟妙妙在一起,小堇就覺得很滿足了。
小堇想變成像妙妙這樣的女性,美麗、優雅而又事業有成,對妙妙的愛慕越來越深,更是喜歡妙妙臀部的曲線,喜歡她像雪一般純白的頭髮,而她的陰毛卻是與白髮形成強烈對照的漆黑,美麗而迷人;她無法停止想像那包在黑色小內褲裏的性感。妙妙讓她感覺到面對男人時所沒有的性慾,希望妙妙緊緊用力擁抱她,想把一切都交給她。小堇應妙妙之邀,兩人一起工作,由一週3次進而成為正式職員,當妙妙的貼身秘書。小堇為此改變穿著打扮,不再是以前那邋里邋遢的樣子,變得美麗而洗鍊,連菸都戒了,學會說義大利話,學會選葡萄酒的方法,也會使用電腦了。小堇生活作息變得正常卻失去了自我,覺得「像在沒有沒有引力的牽絆下,一個人獨自漂流在黑漆漆的太空裡似的」,連自己在往什麼方向前進都不知道。後來,小堇和妙妙到歐洲出差及旅行,先去義大利和法國,再轉到友人在希臘一個島上的小別墅渡假。
小堇想清楚告訴妙妙,自己在追求什麼,表白內心的愛意,想擁抱妙妙也想讓妙妙擁抱,乃至於必須和妙妙相交,因為再繼續這樣下去,她一定會不斷地再繼續失去。可是她擔心不被妙妙接受,如同山姆.畢金柏導演《日落狂沙》的演員對白:「聽好噢,小姐,人被槍擊的話,是會流血的。」
喜歡追根究柢的小堇,聽了妙妙14年前在瑞士頭髮一夜變白的往事,她對妙妙的愛已經無法遏抑,當天深夜,她落入失心狀態,向妙妙告白,忍不住去碰妙妙的身體,小堇腦子裡一面浮現躺在旁邊的妙妙的裸體,一面想抱她,其中有期待、有興奮、有放棄、有迷惑、有混亂、有膽怯,情緒一會兒高漲一會兒低落;忽而覺得一切都會順利,忽而覺得一切都會行不通。儘管妙妙並未拒絕,但妙妙的身體無論如何就是無法回應。這讓小堇簡直像決了堤般地哭泣起來;如同中槍流血。22歲的小堇無法接受殘酷的事實,隔天就像煙一樣消失無蹤了。前去希臘協尋的「我」,在小堇留下的磁碟片文件中似乎找到了答案:「為了避免衝突,我們該怎麼辦才好呢?從理論上來說,那很簡單。作夢啊,繼續作夢。進入夢的世界不要出來,在那裡永遠活下去。」
(四)妙妙無法回應小堇
和小堇初識時,39歲的妙妙並不刻意隱藏自己的年齡。因為皮膚美,身體也結實,稍微化妝一下,或許可以顯得像不到30歲,但她沒有刻意做這樣的努力,很坦然接受年齡所自然浮現的東西,讓自己巧妙地和歲月同化。她脖子像植物的莖一般細,身上一點贅肉的痕跡都沒有;修長苗條,臀部緊縮,看來簡直像工藝品般;且舉止優雅,聰明迷人。唯其頭髮雪白而染黑,不讓人知道。
妙妙的父親是韓幗人,經營貿易事業有成,回饋韓國的家鄉,捐錢興建設施,當地廣場甚至樹立了她父親的銅像。妙妙生在日本長在日本,又到法國巴黎音樂學院留學,不過父親因為癌症去世,母親身體又弱,日語也不太流利,弟弟還在讀高中,所以妙妙放棄成為鋼琴家的夢,回到日本管理公司,成為公司負責人。妙妙結了婚,公司代表人名義上還是她,實務則由大她5歲、曾在漢城大學經濟系留學兩年的日本人丈夫主導負責,她反而專心做公司之外屬於她個人的工作,如大宗葡萄酒進口,或是音樂方面相關活動的安排,在日本和歐洲之間來來去去。
以前,即使妙妙上日本學校,和日本朋友一起玩耍長大,但對妙妙來說,她在日本終究是外國人,於是認為要在這個世界活下去,自己不能不努力獨立自強;也由於太習慣於自己很強,缺乏溫暖的心,沒能試著去了解那些比較弱或是遇上不幸的人。17歲時,妙妙失去處女,然後跟絕不算少的人睡過,卻從來沒有愛過一個人──從來沒有一次真心愛過誰。
妙妙從年輕時就習慣一個人旅行,14年前,妙妙25歲,經歷了一個不可思議的事件。那年夏天,她尚在巴黎學琴,決定一個人暫時住在瑞士靠近法國邊界的一個村子裏,參加當地音樂節,感覺一切美好。直到認識離婚的西班牙英俊男子費迪南,漸漸從他身上聞到性慾的氣味,感覺他如影隨形,這使得原本安靜的村莊生活受到威脅,她想提早離開,卻因房租預付一個月,且在巴黎住的公寓暑假亦已短期租出去,加以並沒有實際發生什麼事情,於是仍然留了下來。一晚,她心血來潮,去村外那有著觀光纜車的遊樂場,管理纜車的老人提醒她,營運時間將屆,這是最後一趟了。未料纜車動力突然停止了,妙妙被困在高處,關了一個晚上,無人察覺,求救無門。她在纜車內用望遠鏡找到自己的公寓,竟然看見房間裏另一個自己的身影,而且房間裏有赤裸男人,正是費迪南!女人隨他擺佈,任他愛撫,全然開放地享受著淫慾,一切的一切都像中世紀某種寓意畫般怪異地誇張,感覺充滿惡意。房間內的他們知道纜車上的她正在看,她儘管噁心想吐,眼光卻移不開;到最後,那男人甚至變成不是費迪南了。
隔天大清早,遊樂場工作人員發現妙妙昏倒在纜車裏,送她到醫院治療。警察把管理纜車的老人帶走,老人完全不記得臨關門前讓妙妙搭上觀光纜車的事。只是,才一夜之間,妙妙的頭髮一根不剩地全部變白了;自此以後,妙妙開始染髮,周圍沒有任何人知道。直到兩人長久旅行,每天生活在一起,小堇才因此發現妙妙染髮。來到希臘小島上,妙妙停止染髮,頭髮好像剛剛開始下而即將積厚的雪一般純白。這個神秘事件,妙妙曾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說過,連她丈夫都被瞞在鼓裏。直到小堇追根究底,妙妙才勉強說出這個保守多年的秘密。
發生這件事之後,妙妙分裂為二,現實的妙妙留在「這邊」,另一非現實的妙妙,或是另一半的妙妙,卻移到「那邊」去了。暑假結束,妙妙沒有回到大學,她停止留學,就那樣回到日本,從此不再碰鋼琴,失去奏出音樂的力量;而且她體內有什麼永遠消失了,也已經無法跟世界上的任何人擁有肉體關係。
29歲時,妙妙告訴現在的丈夫,自己無法性愛,所以不跟任何人結婚。可是,丈夫愛她,即使沒有肉體關係,也希望能夠跟她分享人生。妙妙從小就認識他,總是懷有安穩的好感;不管採取什麼樣的形式,以共同生活的對象來說,除了他之外想不到還有什麼人;又,以現實言,家族公司要經營下去,「結婚」這形式具有極重要的意義。是以妙妙還是結婚了,住東京,自己另有專屬辦公室,與丈夫每週六見面,夫妻基本上相處得很好,感情像朋友,能夠以生活的伴侶共度無拘無束的輕鬆時刻;彼此談各種事情,人格上也互相依賴。唯夫妻之間沒有性關係。
妙妙沒有同性戀傾向,但她非常喜歡同性戀的小堇,跟小菫心意相連,在一起感覺多麼輕鬆愉快,即使兩人以赤裸的身體對看亦安詳自在。直到小堇向她告白,表明愛意,珍惜地觸摸、需索她的身體,因為她喜歡小堇,心想如果小堇那樣會快樂的話,不管小堇要怎樣,她都沒關係。儘管如此,妙妙卻已經不是14年前完整的人了,現在的身體和心不在一起,興奮的只有她的心臟和頭腦,身體卻一直拒絕小堇,像石頭一般乾乾硬硬,不肯接受小堇。也因此導致小堇的失蹤。
事件之後,妙妙、小堇和「我」彼此都失去聯繫。過了半年,「我」坐在計程車上,在東京街頭看到車陣中駕駛Jaguar的妙妙,她跟以前一樣漂亮,極其洗鍊;頭髮白得令人倒吸一口氣,讓人不容易接近,散發著甚至可用神話性來表現的毅然堅定的氣息。特別是那頭髮純粹的白,如同人骨的顏色。「我」感覺,妙妙簡直只剩空殼子一樣,有什麼非常重要的東西已經在她身上徹底地消失了,留下來的不是存在,而是「不在」。妙妙永遠遺失了另一半的自己,整個人似乎「空」了,怎不令人黯然神傷!
(五)人造衛星象徵孤獨
《人造衛星情人》最重要的象徵正是「人造衛星」。小堇和妙妙同時出席小堇表姊的婚宴,正好同桌相鄰,小堇談起美國作家傑克.克羅阿克(Jack Kerouac)的小說,妙妙誤認是「寫人造衛星Sputnik的那個人」。由於「人造衛星」這個話題,此後,一見鍾情的小堇就在心裡把妙妙稱為「人造衛星情人」。
關於人造衛星,1957年10月4日,蘇聯從哈薩克共和國太空基地發射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枚人造衛星──Sputnik 1,它圍繞地球運行時所發出「嗶……嗶……」聲的無線電訊號,轟動了全世界。Sputnik是俄語,以英文來說,是「旅行的伴侶」(traveling companion)之意。1957年11月3日,蘇聯再發射一枚體積較大的人造衛星──Sputnik 2,這個人造衛星載有一隻名叫「萊卡」的狗,是第1個進入太空的地球生物,然因衛星無法收回而成為太空生物研究的孤獨犧牲者。「人造衛星」這個話題,使得小堇想起,「在太空的黑暗中無聲地飛行的人造衛星。從小小的窗口往外窺探的小狗那一對明亮的黑眼睛。在那無邊的太空式孤獨中,小狗到底看見了什麼呢?」
當小堇向妙妙告白,妙妙雖然心裏有些高興,身體卻僵硬而無法回應小堇的撫觸,妙妙以人造衛星來譬喻兩人之間的關係,告訴前來希臘協尋的「我」,說:「我那時候可以了解。我們雖然是很好的旅行伴侶,但終究只不過是各自畫出不同軌道的孤獨金屬塊而已。從遠遠看來,那就像流星一般美麗。但實際上我們卻個別封閉在那裡,只不過像什麼地方也去不了的囚犯一樣。」小堇留下的磁碟片文件,同樣提到人造衛星:「就像兩個重疊的人造衛星一樣,我緊緊貼在妙妙的身旁,和她一起漂流到什麼地方去。」
妙妙與小堇就像人造衛星,各自孤伶伶獨自繞著地球團團轉,這樣一堆金屬顯得多麼孤單、可憐。即使當兩顆衛星的軌道碰巧重疊時,兩人就這樣見面了;或許心可以互相接觸,但那只不過是短暫的瞬間;下一個瞬間,她們又再度回到絕對的孤獨中,直到有一天燃燒殆盡為止。
大老遠趕去希臘的「我」,未能幫忙找到失蹤的小堇,離開雅典之前,「我」深切感到,無論自己或是小堇、妙妙,都是孤單的。妙妙愛小堇,但無法感覺性慾;小堇愛妙妙,而且感覺到性慾;「我」愛小堇,也有性慾的感覺;小堇雖然喜歡「我」,但並沒有愛「我」,也無法有性慾的感覺;「我」對別的女人能有性慾的感覺,但並不愛她。以上關係非常複雜,簡直像存在主義戲劇的劇情一般。一切事情彷彿都堵在那裡行不通,誰也到不了任何地方,無可選擇,而小堇更是獨自從舞台上消失了。「我」內心不禁吶喊:「為什麼大家非要變成這麼孤獨不可呢?」「難道這個星球是以人們的寂寥為營養繼續旋轉著的嗎?」「我」躺在平坦的岩石上眺望無垠的天空,尋找著人造衛星的光,想著以地球引力為唯一連繫牽絆、繼續通過天空的Sputnik的末裔們,它們以孤獨的金屬塊,在毫無遮擋的太空黑暗中忽然相遇,又再交錯而過,並永遠分別而去,既沒有交換話語,也沒做任何承諾。回到東京,「我」在半年後看到了白髮如雪的妙妙,不禁感嘆,「已經徹底變成一個完全不同的人了,我們還是可以像這樣默默地過活下去,可以伸出手把一定限量的時間拉近來,再原樣把它往後送出去。把這當作日常的反覆作業──依情況的不同,有時甚至可以非常俐落。」只是,「我」越是這麼想就越加空虛了。
《人造衛星情人》彷彿告訴大家,也許有機會遇到完全契合的伴侶,可以感覺彼此的心跳,但會否只是運行於不同軌道的人造衛星?終究只是暫時的相逢,短暫交會之後,仍要運行在彼此不同的時空中……,註定各自孤單寂寞地過一生。人造衛星之象徵孤獨,以及「人造衛星情人」之註定悲哀命運,怎不令人感喟良深。
(六)「這邊∕那邊」的對立
結構主義論者羅蘭‧巴特(Roland Barthes)認為,象徵意義的產生,往往來自「區別」或「二元對立」,小說裡的「對立」,會逐漸發展成為龐大的對立模式,籠罩整篇作品,並左右其意義,謂為象徵語碼(Symbolic Code)。村上春樹作品中屢有「彼∕此」的對立,具饒富深思的象徵意義,如《尋羊冒險記》的「我」在老友「老鼠」父親於北海道草原別墅的一面大鏡子前,看著映在鏡子裏的自己,變成自己是鏡子裏映出來的像,正在看著真正的我似的;再如《黑夜之後》一是在房間內沉睡不醒的姊姊惠麗,一是攝影機前畫面中惠麗的影像,彼此似乎暗藏著說不出的意義。至於《人造衛星情人》中妙妙「二重我」的分裂,亦即「這邊的我∕那邊的我」的對立,而且由現實的「這一邊」移動到非現實或異界的「那一邊」,如此不可思議的「越境」成為本書的最大特徵,讓人咀嚼回味不已。論者謂,「異界」之旅是村上春樹作品中的重要主題之一,其小說人物因為自閉的關係,與他人產生距離,結果身邊的人不斷地離去,導致身邊沒有可以交心的人,無法透過與他人的相對化來意識到自己,進而喪失對所處時空的感覺。是以如果沒有「異界」,小說人物就可能會一直陷在自閉狀態中,唯有透過與「異界」的相對化,意識到現實世界的重要性,找回對時空的感覺,並從自閉狀態中振作起來。
25歲那年夏天,由於受困纜車事件,妙妙整個人被撕裂成兩半,她告訴「我」,「我留在這邊。但另一個我,或一半的我,卻移到那邊去了。帶著我的黑髮、我的性慾、生理、排卵,還有或許連我生的意志之類的東西一起去了。而留下來的一半,就是在這裡的我。」換言之,她把另外一半的自己,遺落在瑞士靠近法國邊界的一個小村莊裡,現在這裏的妙妙已經不再是完整的人了。
受困於纜車時,妙妙用望遠鏡看到房間裏的自己和那個男人,她在這邊,另一個她在那邊,「這邊的她」眼睜睜看著那個男人對「那邊的她」隨心所欲地擺佈,做了所有淫慾的事。「這邊的妙妙」一方面對自己所看到的感到噁心,一方面又懷疑,「這邊的我∕那邊的我」誰才是真正的我?是接受男人的我?還是厭惡男人的我?妙妙可以說已經無法判斷了。14年後,妙妙告訴愛著她的小堇:「我過去曾經活過,現在也還這樣活著,現實上和你面對面談著。但在這裡的我,並不是真的我。你眼睛所看到的,只不過是過去的我的影子而已。你是真的活著,但我不是。」妙妙已經分裂為「這邊的妙妙」和「那邊的妙妙」,小堇不但愛著這邊的妙妙,也愛著那邊的妙妙。妙妙的分裂,同樣投影為小堇的分裂,決定由這邊去到那邊。
聽了妙妙的述說,以及看了小堇磁碟片文件,「我」終於想通了這難以置信的一切。「我」如此假設,穿過鏡子,小堇到那邊去了,既然這邊的妙妙無法接受小堇,所以小堇一定是去見那邊的妙妙了。「我」想像著「那邊」的世界,也許小堇在那邊,失去的另一半──有黑頭髮、有潤澤性慾的妙妙也在那邊,她們在那裏相遇,終於能夠互相填滿,做著語言所無法做到的事。村上春樹藉由「這邊的我∕那邊的我」的對立,揭示人們內在並存的善良與邪惡、光明與黑暗,讓讀者進而省察自我,更是對於社會道德的一種質疑或批判。
閱讀村上春樹的小說,總帶給人們無限的迷惘;同時也為現代人內在無法排遣的孤寂,感到心有戚戚焉。在這般的孤獨中,又如何才能夠十足地生存下去呢?村上春樹《人造衛星情人》的人物,彼此無法身心擁抱融合,整個人「空」了,甚至於選擇自「這邊」的現實世界消失,或是情願留在「那裡」的夢中,怎不令人憂傷!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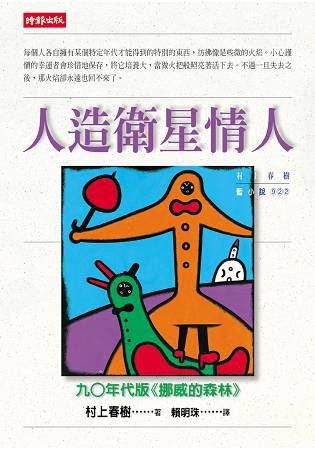


 留言列表
留言列表


